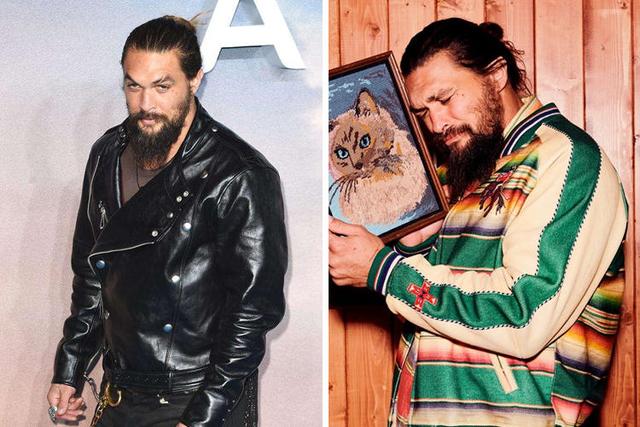那个国内首开同性恋课程的教授要退休了
时间:2018-02-03 16:52出处:资讯阅读:209
文 | 特约作者 姚冰淳 向思琦 刘莼 赵佳宁 洪婉琳
这是高燕宁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了。这位将满60岁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只想把剩下的课认真上完,“在教师的位置上,我已经尽力了。”
对于艾滋病研究、性与性别研究和公共卫生教育改革来说,他退休后留下的空白还没人再填补。
高燕宁1999年初涉艾滋病领域。自2001年秋起,他在陆续教授多门国内首开的新型学分课程,包括《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健康社会科学总论》和《边缘人群健康干预》等。这些课程,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侧重性与社会性别的理论与实践,希望在传统公卫领域之外探索现代公卫问题的现实挑战和应对机制。
|
| 2002年7月进村(中间为高燕宁)。图/受访者提供 |
在他之后,与“性与性别”相关的课程在高校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酷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类性学》、中山大学的《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等,多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在医学领域,虽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逐渐为主流医学所推崇,但当下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课程结构仍被生物医学模式所主宰,少有在公共卫生课程中引入人文视角。
2002年6月,高燕宁深入中原艾滋村进行社会调研,成为高校公开带着课题进入河南艾滋村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刚结束的2017年秋季学期,高燕宁开《边弱群体健康促进》这门研究生课程,每次七八人,加上三四个旁听生,往往是知和社(复旦大学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学生社团)的成员,分散地坐在教室后半部。
|
| 2003年1月16日,和武书记、艾滋村村民。图/受访者提供 |
一节课,两小时十五分钟,两三百页幻灯片,不休息,中途只喝一口水。高燕宁上课中气十足,又兼有活泼天真的情态,全然不似花甲将至。问到一些挑战常识或是学生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比如“人类有独立的性系统吗?”,他会微微笑起来,刻板的嘴角纹消失,眼里透出点狡黠的光。
学生们猜不出他的年龄,更没有人知道他心脏不好,甚至随时可能停跳,总以为他虽比常人更削瘦一些,但“骨子里有劲儿,可敬可亲,身体硬朗”。
退休后,除了《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原本由高燕宁首创和主持的课程可能没有了继承者。国内最早对同性恋进行大规模艾滋干预的学者、首届“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张北川感到很遗憾,“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位置,他能够弹奏的琴声可能就没有了。”
沪上第一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律师周丹和他说了几乎一样的话,“现在高老师要退休了,那怎么办,我要问的是,以后中国高校性教育、艾滋病教育,到底谁来科学地做?”
采访中,“我是学医的”——这个身份标识,被高燕宁重复了十几遍。在他眼中,“学医”二字意味着良心。
|
| 上课。图/受访者提供 |
“救命啊”
如果没有进入艾滋病领域,高燕宁可能不会见证如此多的死亡,也许不会背负着如此沉重的使命感。
1958年出生于广西省武鸣县的高燕宁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典型。政治浪潮与时代命运同时作用于他,经历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他说:”从那个时代过来,对艾滋村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1966年到1976年,8岁到18岁,文革贯穿高燕宁最重要的成长期。他还记得有天放学经过五海桥,看见一群人喊着口号把装着一个人的猪笼扔进河里。“笼子是绑死的,那个人竟然过了几十米以后挣脱笼子钻出水面了。我看到两个民兵拿着枪一直追着打。那人的脚被绑住,他踩着水朝对岸游。大概离对岸还有几十米左右,有颗子弹打在水面上,子弹的浪花溅出水面,人沉了下去,血水染红黄色河水。” 几十年过去,那一幕的回忆依然震撼:“人怎么可以被这样对待?”
14岁那年,工人宣传队进学校,高燕宁失学做了半年“散捞”(打零工),挖土一天一块二,晒桂圆肉一天八毛。父亲能听到他晚上睡梦中的叹息声。武鸣高中和家隔着灵水,少年人求知若渴的目光常常越过灵水,牢牢停留在夜色里教室的灯火上,“想读书哇”。初中的老校长把他从失学痛楚和散捞流落中“打捞”起来,进了补习班,再和下一届一起读了高中。
童年父亲挨斗、下放改造;家庭破裂、母爱顿失,他觉得自己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如‘狗崽子’和‘野仔’一般”,是老校长和另外两位老师慢慢给了他一点勇气,在心里把头抬起来,并从人的意义上看待自己。
文革之所见和自己的经历,都成为高燕宁关注和思考普通人命运的起点。他一生都对三位老师心存感激,日后他在艾滋村助学,在大学课堂里讲学,似在冥冥中传承和回报了他们。
|
| 最后一次进村时拍的陈亚洲的家。图/受访者提供 |
1977年,高考恢复,19岁的高燕宁考进了广西医学院卫生系。辗转打听后,他才知道卫生系有别于临床医学,未来可以做研究。以此为起点,从广西医学院到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与复旦合并),他在卫生统计学领域做了近20年的学问。
1999年,高燕宁获得前往泰国玛希隆大学学习健康社会科学的机会,转入艾滋病领域。当时艾滋病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男性同性恋、性产业、吸毒方面都已经有学者做出了些成绩,只有社会支持体系是个空白,于是他选择由此入手。
2000年,高燕宁向复旦申请课题《未来十年中国艾滋病社会支持体系对策研究》时,知道了艾滋村的存在。同时,他在复旦开出了《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课程,也希望给学生带来一些来自现场的观察。
这一年,距离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已经过去十几年,相较于第一批进入艾滋病领域的国内学者,高燕宁觉得自己“已经晚了”。但他仍是第一个由高校公开带着课题走进河南艾滋村进行研究的。
血液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1979年,单采浆术在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推广至全国。单采浆术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放入离心机中分离血浆和血球,再将血球回输。400cc的血能换50元营养费,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纷纷撩起袖子伸出手臂,“潘多拉之盒打开”。因设备昂贵,做不到一人一套,操作规程也不完善,大规模感染就在这一抽一输之间发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疫情在中原爆发,河南省的许多村庄,被打上“艾滋村”的标签。卖血常常是一个家族的集体行为,一旦艾滋病病发,意味着一个家族全部被摧毁,村民无力自救。
2002年6月,高燕宁踏进河南艾滋村。第一天进村,在村头遇上村民,同行的村医递上烟打招呼。走过不远,村医告诉他,刚才那些人,全是感染者。
看的第一个病人,35岁,和她同岁的丈夫两个半月前刚刚因艾滋病去世,留下她和年仅10岁的女儿。听到高燕宁一行人的脚步由远及近,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呐喊:“救命啊!救命啊!”
村里道路泥泞、鸡鸭乱飞,房子东倒西歪,有的村民家锅烂了也修不起,把面粉弄成糊糊,去补锅上的窟窿。有瘫痪的老人住在牲口棚里,拖着脚爬去门口拿吃的,“爬进爬出的地方都磨光滑了”。高燕宁第一次看到“养老人像养牲口一样”。
每遇到一个病人,他就递出一个复旦大学的信封,里面装着50 元访谈费和自己的名片。他不知道此行后还能不能再来,如果村民需要帮助,可以打电话给他。
信封一个接一个发出去。虽然进村前已有心理准备,但进村第二天,他回忆起当时已经连说话、思维的力气都没有了。学医的人见惯生死,原来从不做噩梦的他,晚上睡觉,“脑袋里就像有个白炽灯,眼前都是亮晃晃的一片。”
五天后,高燕宁出村时,一个穿红衣服的村妇骑着自行车从远处飞驰而过,他忽然觉得,自己走出万人坑,活了过来。
几周后第二次进村,高燕宁选择夫妻双方都是病人、孩子还很小的家庭做深入访谈。下半年,得益于他所做的调查,疫情被逐渐了解,中国首批二百人份进口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其中三十份,给了他进行调查所在的王营村。
除了做访谈,高燕宁每到一户人家,都会为他们拍全家福和生活照,在下一次进村时捎给他们。而当他带着照片返回村庄时,照片里的人,却常常已经不在了。
进村六年,冬子(化名)是他见到的唯一幸存者,也是与他打交道最多的艾滋病人。收到照片时,冬子很感激:“多亏好多照片,让我还能有些东西可以回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就放不下自己的小孩。”冬子的话让高燕宁开始明白,比起自己的生死,村民们更在乎子女的未来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死而断送。因此,帮助孩子们上学,在高燕宁眼里,成了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对策。
病患和孩子数量庞大,而个人的力量微弱。孩子加入助学名单的机会有限,村民看到自己的孩子没能进入助学名单,就有可能情绪激动。甚至到高燕宁住的宾馆,一间房一间房地拍门找他,“你怎么不资助我?”“你们偏心眼!”。他要不厌其烦地解释要求和流程。
2006年3月,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开始施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2008年7月中旬,艾滋村的疫情已经稳定下来,高燕宁最后一次进村。
他来到曾经的访谈对象陈亚洲的家,高高的门庭,大门紧闭,门上还见得到绿色的春联。这是当地的习俗,说明这户人家在有人离世后已经过第二个春节了。透过前院半人多高的砖墙,他又看到了六年前自己为亚洲第一次拍全家福的堂屋门口,只是已经人去楼空。在村头的玉米地里,他找到了刘亚洲夫妇的墓地,他曾和他们一起在那里补苗。
“要做的不仅仅是开药方”
2001年起,高燕宁着手筹备讲授相关健康课程。2002年到2008年,每年高燕宁半年进村,半年在复旦开课。
他请来国内众多知名学者来讲课: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白先勇等,课堂常常爆满。他也带学生去同志酒吧、公园、舞厅等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借助开课,过去从自己老师那里的所得被“重新赋值和投射”到自己的学生,希望学生能够消除歧视和偏见,“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人”。
他在课上讲同性恋、讲异装癖、讲小姐、讲艾滋病人、讲男公关、讲嫖客……讲被主流排斥、歧视甚至可能侮辱的边缘群体。他笑称自己也是“边缘群体”。
首次进村的2002年,他开出的《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是国内医学院校第一门从人文社科视角来讲艾滋病的综合课程。
2003年的《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则成为中国高校历史上第一门同性恋主题课程。开课计划上报后,当时复旦研究生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反复讨论,最终经校党委特批通过。
为什么想开这样一门课?高燕宁对记者说,现在一方面是医学教育缺失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医学生常常很容易计算出A行为跟B行为(现象)有统计联系,却又很难说出这种联系在社会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他解释,研究同性恋群体的健康问题、实际上可伸展到多个(边缘、弱势或少数)族群,可以从人性、人文展开,给学生补上人文情怀和社科素养这一课。
2003年-2004年《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正式选课人数只有5人。当时的课程助教,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师梁霁回忆说,研究生选课更考虑学分、更实际些,而且十几年前还没有那么开放,学生可能会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但请来的一众知名学者吸引了1745位学生、老师和校外各界人士前来旁听,并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东方早报》给了一整个版面,标题为“寻求宽容:同性恋课程复旦开禁——中国同性恋群体渐渐走出冬季”。
高燕宁回忆,当时选《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一名学生课前曾表示对同性恋“是有恐惧心理的”,选课也只是听从导师建议,但课后却表示,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也应该尊重“他们”。
有学生说直到大三仍不知公卫人可以做什么,但在他的课堂上开始思考“医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开药方——医者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也一样必要。”
复旦首开《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之后,数所医科大学公卫学院也陆续开起相关课程。受高燕宁启发,2005年,复旦大学开出了《同性恋研究》的本科生公选课,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课程也增大同性恋内容比重。
2011年,高燕宁在艾滋病、同性恋两门课基础上进行整合,开出《性健康社会科学》。他提前半年,每天花八小时准备,不敢和任何人打交道,神思张悬。第二第三年开同一门课,即使是做资料补充,每天也要五个小时,用“五笔”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备课、写文章时看完一本书就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来不及收拾。
在高燕宁看来,这门课不仅是开课数的量变,更是课程结构的“质变”,将性别理论、防艾和理解性少数群体所需的人文社科内容重新结合。
“我过去的三门课,几年下来,听课的学生超过一万人次。”这是他惯常谦逊的谈话间,少有露出一点骄傲神色的时刻。
另一次,是讲到把“性与性别”的概念引入公共卫生领域,“我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公卫学院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讲‘性与性别’能达到我这个水准。中国公卫学院要整体上达到我这个水准,十五年以后。你看吧,十五年以后他们就在走我这条路,一定的,一定的。”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就已启动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卫生专业课程的全球规划,从性健康现实切入,改变性与文化剥离的状况,向医学研究生系统讲授性(Sexuality)和性别(Gender)的基本理论知识。而国内这样做的学者寥寥无几。
高燕宁说:“我作为老师,不敢怠慢学生。”最后一堂课,学生轮流报期末论文的选题,他会走到靠近学生的位置坐下,边听边记,不时与学生讨论。讲完后,再挪到下一个学生的身边。
他会用很多不太会出现在传统公共卫生课堂上的材料来讲课。《边弱群体健康促进》的“解构色情”一课里,他把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提香的《乌尔宾诺的维纳斯》打在投影幕布上,讲色情目光与观赏艺术。
在复旦,高燕宁一共只带过两个研究生。02级公卫的一位本科生曾两次到他办公室,拐弯抹角地表示想做他的研究生,“你的事情总要有人来继承吧。”他没答应,“我知道,这个社会面对艾滋村的问题时有多少困难”。
身体状况也成为教学路上的困难之一。2010年他在学校体检时,查出了心律失常,“停跳8-12秒是家常便饭,停跳4-8秒更是每天几十上百次之多” 。最痛苦的时候,他靠种菜纾解,慢慢缓过来。二十几平米的阳台上,放满种菜的花盆。
过去一茬一茬的学生和旁听者门庭若市,他生病休养了三年后开课,不再进艾滋村而专注于“性与性别”方面的教学,听课者却已寥寥。身体原因让他无力参与除教学外的其他学校事务,所以学生很少知道他,更不了解他进过艾滋村,而他也不再有经费请知名学者来讲课。
曾有同事评价高燕宁的研究方向,“偏到人文社科中去了。”这被认为或许也是他在公共卫生学院选课人数少的原因,他不在意,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在面临艾滋病的挑战之际,传统的纯医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越来越无法胜任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国际上主流学界已日益强调“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参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潘绥铭说:“高燕宁率先尝试了艾滋病领域中的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教育,不仅为预防艾滋病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跨学科研究与教育这一国际最前沿的学术发展趋势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退休后,高燕宁主持的《性健康社会科学》和《边弱群体健康促进》两门课将不再继续。他明白自己改变不了世界,一门课也改变不了多少人。“一分耕耘,半分收获”,尤其是在“边弱群体”的公共卫生教育这件事上。可他看到了必然的趋势,并不着急。
张北川很痛惜鲜有人知道高燕宁的贡献,“难就难在这里,走得太前面,就没人知道了。”
“最伤心的学问”
进村调研的六年间,高燕宁救助了许多患者和他们的孩子,但他说,艾滋村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好,也“最伤心的学问”。
即使现在,高燕宁的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也始终避免着情感刺激。他还要学习控制情绪,但过去艾滋村的人事随时随地可能击中他,“突然有个东西出现在脑海里,就有眼泪要流下来的感觉”。
2016年,高燕宁开始动笔,记录在艾滋村6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思。他想把这本书献给艾滋村民,“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或不再长大成人的孩子们”。
他不得不重启痛苦的回忆。他害怕因情绪波动导致心脏停跳,写书的十个月,思维紧绷,仿佛走钢丝。完稿时,他不由得掩卷长叹,不忍回首。
高燕宁喜欢画画,有退休后学一学的打算。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艾滋村的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我觉得无能为力”。他曾说艾滋村的故事如果一天讲一个,他能讲一千零一夜,“每个故事都那么的痛、那么的冤,听的人听不下去,看的人看不下去,讲的人讲不下去。”而现在,“一切又回归沉静,静得出奇,静得让人信以为,这世界真的什么也没发生过”。
据河南上蔡县原防疫站站长武庭秀介绍,现在政府会发放进口的抗病毒药物给艾滋病病人,大部分病人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村里的条件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曾经蒙受苦难和歧视、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病人,再无法享有这一切,令高燕宁扼腕的是,他们的故事也随着生命的逝去被渐渐遗忘。
张北川认识许多进过艾滋村的学者,只有寥寥几人通过出书的方式为河南的血祸留下真相,高燕宁就是其中之一。“孜孜以求探索真相、记录真相并追求真理,这是学人的使命之一。高燕宁没有辜负这种使命。”